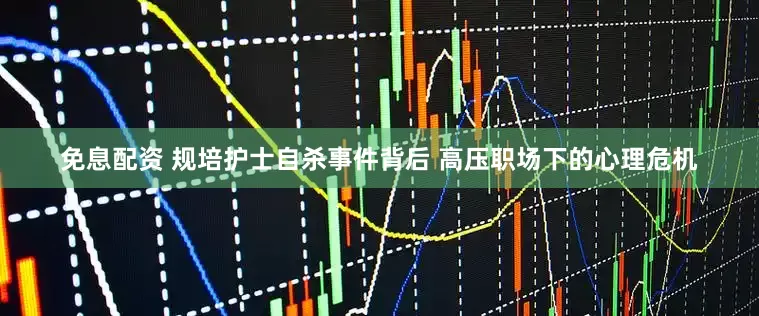
苏诗雨在跳楼的19天前,她在手机备忘录里留下遗言,“求你们,不要救我。”去世两天前,她再次写下“不要救我”。姐姐发现后,与她聊了好几个小时,内容围绕着“这个班还要不要上了”。

此时,苏诗雨成为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(以下简称五官科医院)的规培护士刚满五个月。所有亲近的朋友都知道她的工作压力很大,频繁加班,还要应付考试、抽背和做科研。其间,她因数次出错不断被责备,手机聊天记录里提到“压力”有155次。

这不只是一个规培护士的故事,还是一个敏感内耗的年轻人卷入高效率、快节奏职场,无法适应也无法逃离,最终自信被摧毁、走向极端的故事。

2024年12月27日,苏诗雨早上6点多出门后,家人再也没见过她。7点55分她到达五官科医院,8点20分护士长与她在会议室进行了近40分钟的谈话。当时,苏诗雨还在病假期间,她因确诊抑郁症休假,但她急切地想重返工作。护士长劝说等状态调整好,再安排她离开手术室,转去病房上班。

五个月前,20岁的苏诗雨从上海一所大专学校的护理专业毕业,成为五官科医院手术室的一名规培护士。好友小曼不大支持她当护士,这一行虽然收入还行,但是太累了。不过她理解苏诗雨更看重稳定,“她说当护士不用给家人太多压力。”

苏诗雨的父母是20世纪90年代从安徽来上海谋生的,30多年来在菜场以卖猪肉为生。19岁时,家里因为疫情中断了生意,奶奶、父母接连生病,她一边申请助学金,一边找各种兼职。得知自己入职五官科医院时,苏诗雨开心地抱着妈妈转了一圈。然而,入职后的几个月里,她努力工作却总是被责备,很少得到夸赞,自信心一点点崩塌,开始觉得自己“一无是处”。
悲剧发生前约半个月,苏诗雨与小曼见了最后一面。一开始她们一起说笑,拍了很多照片,一切如常。可一聊到工作,苏诗雨就蔫了,低头抠着手指。小曼给苏诗雨支了很多招,但苏诗雨似乎沉浸在自己的焦虑中,满脑子只想着解决在医院的困境。
入职13天,苏诗雨就开始参与手术,作为一名巡回护士,她需要在手术过程中随时为医生提供所需物品,协助处理突发情况。工作时她频繁出错,关系到病人,手术室的容错率特别低。某综合医院眼科主任张瑜觉得有些错误相当危险,比如贴错眼睛。
在那些关于出错的聊天记录里,“快”是被经常提到的原因。苏母记得女儿提过常常一天要做20多台手术,每台手术几分钟到一个小时不等。由于手术间隔太短,中午只能点外卖,在10~20分钟内把饭吃掉。苏父也记得,女儿说为了不去上厕所,水都不敢喝。
作为新手,慢是可以被理解的,但慢又是很难被“原谅”的。陈美美说,慢了,器械间就要打架,这台手术还在用,下一台手术只能等着。被影响的还有主刀、医助、麻醉师等所有参与手术的人的时间。有的医生还要坐门诊,时间耽误了,门诊病人也会不高兴。
带教难题也是导致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。进手术室前的培训是空泛又浅显的护理知识,而各种各样的考试和抽背都没有针对手术实操。陈美美说,病房护理的知识点在学校会有涉及,而手术室的知识则需在规培期学习。一份聊天记录显示,7月30日也就是入职13天后,苏诗雨就开始参与手术了。而她的培训手册中记载,9月初她才开始接受眼科护理入门培训。
赵卓雅想过每天下班后抽一个小时,和学生巩固一下今日所学。但常会有医生改变计划临时加手术,从五六点拖到八九点下班,只能作罢。回家后,赵卓雅还要忙科研——想课题、做数据、找资料、写文章。虽然不是硬性要求,但周围人都在做。该医院的病房护士程丽萍说,作为一家教学型医院,科研任务重,而科研又和晋升挂钩,日渐形成一股风气:大家都在卷科研,便会分担一部分临床的精力。
规培护士也被迫加入了科研队伍,苏诗雨被要求做“质量很高的”科研PPT,她的同事有的帮老师申请专利,有的做科普小视频。“休息时间被占掉,越来越累。”一位规培护士告诉新京报记者。
苏母第一次注意到女儿状态不对是在2024年9月初,女儿一到家就默默回房,很少出来。9月9日,一位同事也注意到了她的反常,在微信上问她怎么“蔫蔫的”,苏诗雨回答状态很差。两天后,她向带教老师提出想换到病房。“在房间实在太压抑了,医生们都很严肃,有时候自己会很敏感,一着急就容易错。”她在备忘录里写道。
11月12日,苏诗雨前往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门诊,症状测评结果显示,被试者重度焦虑、中度抑郁,一周前因工作、家庭、学习问题病情加重。据《上海市医疗卫生人员权益保障办法》第十四条,“医疗卫生机构应当重视医疗卫生人员心理健康,建立心理疏导制度,定期进行心理健康宣传,为医疗卫生人员提供心理评估等服务”。
自杀前一个月,苏诗雨想过其他出路。陈美美提到,2024年11月,苏诗雨打听过做药代的情况。聊天记录显示,她还咨询过做临床协调员的同学,对方回复“也挺烦的”。小曼也记得,苏诗雨问她能否帮忙找找别的医院,“她不是喜欢麻烦别人的人。”小曼猜她是实在没办法了。
这段时间苏诗雨焦虑得要命。看着其他规培护士在群里交作业,她怕跟不上,考试过不了,连规培证也拿不到。在这期间,苏诗雨还在担心因为心理疾病被劝退,病房去不了,手术室也不要她了。她多次咨询姐姐,反复琢磨领导与她的谈话是否有上述猜想的潜台词。
想回去上班,似乎成了苏诗雨生命最后时光的执念,也是她能想到的“战胜心理恐惧”的唯一办法。在休息了九天后,她主动申请上班,“最近状态已经好很多了”,并获得了允许。但她的状态没有变好,下班后,苏诗雨在手术室的卫生间坐了两个小时才回家。隔天凌晨,姐姐被她惊醒,发现她浑身发抖、大哭,不停地抠手指。姐姐不让她再去了。
自杀的前一天,她以保证的方式再次请求去上班,“不用担心,我绝不给你们惹事”,但这一次没有获得允许,护士长劝她再休息一段时间。就在结束谈话的第三个小时,苏诗雨打算做最后一次挣扎,“护士长,我去病房,哪个都行,麻烦你了,后面两天我来上班。”护士长回复,“先不着急来,你的事我肯定帮你落实好,你放心哈。”并附有三个爱心符号。但查看遗物手机的苏听雨发现,妹妹没有点开这条消息。
苏诗雨自杀当天的下午1点左右,她来到一家宠物医院。医院病历显示,下午1点27分小仓鼠心搏骤停,宠物小仓鼠是4年前姐姐送的礼物,曾经也是她的一个支撑。当时接诊的医生回忆,她在手术室默默哭了一会儿。半个多小时后,她从宠物医院附近一栋居民楼的19层天台跳了下去。看了监控的姑父回忆,她径直走进离小区门口最近的一栋楼,从进电梯到跳下,只有15分钟。
同创优配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